- 作者: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 完成日期:2020.10.05
-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 概览:人人都需要食物,大部分人都爱吃食物,可很少有谁敢保证自己了解食物。
- 评分:⭐️⭐️⭐️⭐️
- 类别:历史
书籍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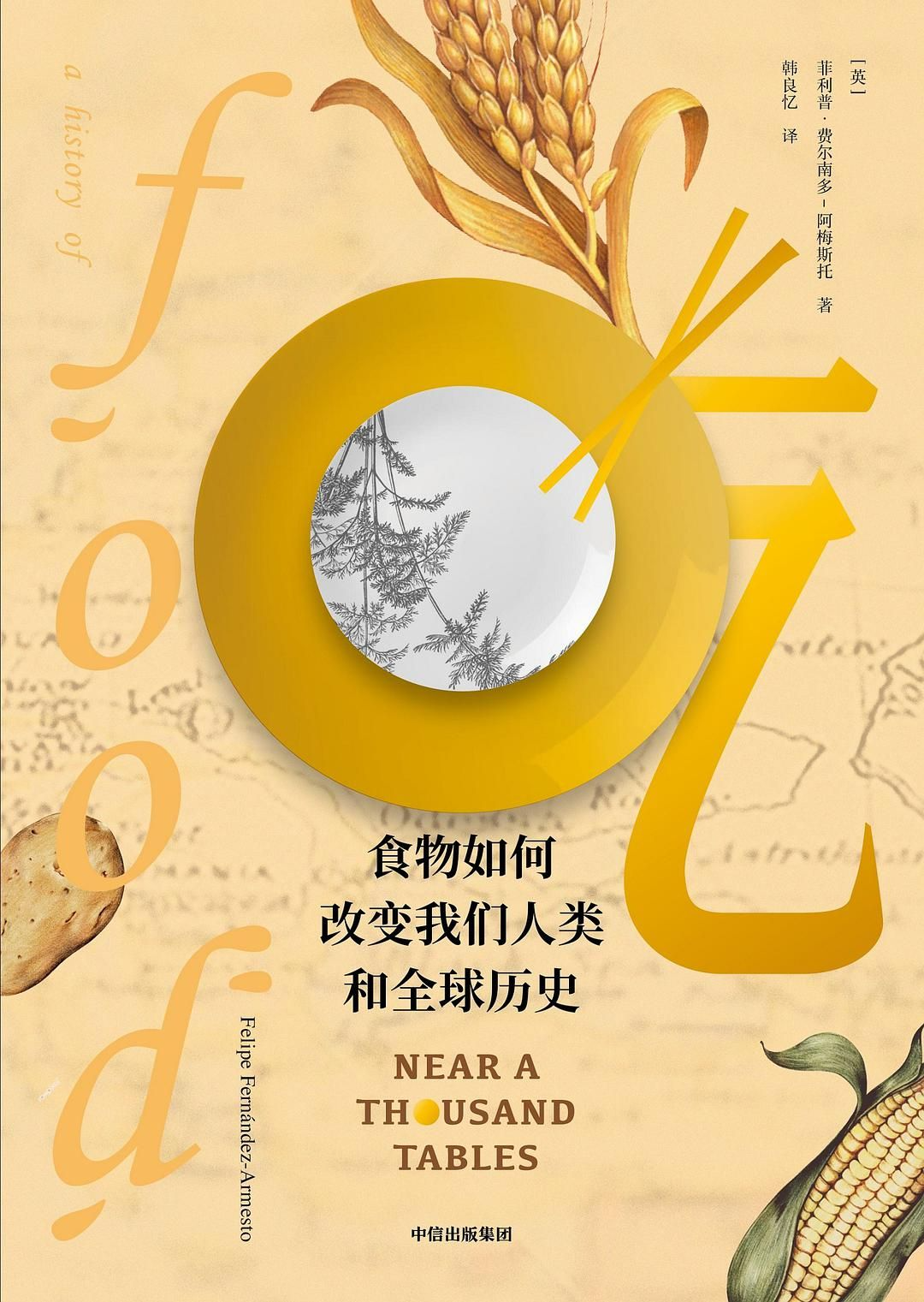
人都需要食物,大部分人都爱吃食物,可很少有谁敢保证自己了解食物。面对满盘珍馐,你看到的或许是卡路里,是营养配比,是价格,而有人却能看出文化标签和历史印记。知名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有言:“告诉我你吃什么,我会告诉你你是什么。”盘中之物承载了人类过去与现在的种种信息:我们的身份,我们在社会中的位置,我们所处的社会在世界中的位置。“吃什么”和“怎么吃”的发展史,也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写照。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在这本令人大开眼界的书中,他重点考察了与人类文明深深交织在一起的八场饮食“革命”,呈现了一部“吃出来的全球史”:火的使用揭开了文明的序幕,人类独有的烹饪技能就此诞生。
书籍摘要
第一场革命是烹饪的发明,我认为从此以后,人类变得有别于自然界其他生物,而社会变革的历史也从此展开。
有位现代的牡蛎专家则是这么说的:你旨在接收“大海锐利的直觉,以及所有的海草与和风……你正在吃大海,就这么回事,只不过在魔法的点拨下,有股奇妙的感觉自那一口吞下的海水中逸散而出”。
例如澳大利亚原住民爱吃木囊蛾幼虫,趁幼虫肥嘟嘟的,体内还有未完全消化的木髓,就将它们自橡胶树上刮下;北极圈内的涅涅特人(Nenet)把自己身上抓下来的虱子放进口中咀嚼,“像在吃糖”;[插图]南苏丹的努尔人(Nuer)情侣,据说会互相喂食从头发里现抓下来的虱子,彼此示爱;东非的马萨伊人(Masai)会生饮从活牛的伤口挤出的鲜血;埃塞俄比亚人爱吃里头藏有幼蜂的蜂巢;
生的食物一旦被煮熟,文化就从此时此地开始。人们围在营火旁吃东西,营火遂成为人们交流、聚会的地方。烹调不光只是料理食物的方法而已,在此基础上,社会以聚餐和确定的用餐时间为中心组织了起来。烹调带来了新的特殊功能、有福同享的乐趣以及责任。它比单单只是聚在一起吃东西更有创造力,更能促进社会关系的建立。它甚至可以取代一起进食这个行为,成为促使社会结合的仪式。
仪式性的餐食成为衡量人生的尺度。
西方最经典的“生”肉菜品就是鞑靼牛排。菜名中提到中世纪时形象凶残的蒙古人,又名鞑靼人(Tatar),鞑靼是其中一支蒙古部落之名。此二字令中世纪的民族志学者联想到古典地狱观念中的深渊“塔耳塔洛斯”(Tartarus),因此用“鞑靼”二字来妖魔化蒙古敌人简直再合适不过。
西方最经典的“生”肉菜品就是鞑靼牛排。菜名中提到中世纪时形象凶残的蒙古人,又名鞑靼人(Tatar),鞑靼是其中一支蒙古部落之名。此二字令中世纪的民族志学者联想到古典地狱观念中的深渊“塔耳塔洛斯”(Tartarus),因此用“鞑靼”二字来妖魔化蒙古敌人简直再合适不过。
以储存这些含有毒素的食物,不必害怕别的动物来抢,等到人类自己要食用前再加热消毒即可。
focus(焦点)一词不论照字面来讲或探究其词源,都意指“壁炉”。人一旦学会掌控火,火就必然会把人群结合起来,因为生火护火需要群策群力。
今日,这种唯“天然”(也就意味着原始)的偏见,让生食在现代都会蔚为时尚,不少都市人早已对时下过度造作的生活方式心存反感,寻求重返伊甸园。文明似已僵化,而有个办法可让人超越文明的限制,那就是恢复生食。浪漫的尚古主义和对生态的焦虑就此结为同盟。
这种新的烹调方式简直反革命到惊人的程度,它彻底逆转了使进食变成社交行为的烹调革命,从此角度观之,它让我们回到进化史上社会尚未形成的时代。
哥伦布在上一次航行中,误把阿拉瓦克人说的Cariba(加勒比人)听成Caniba,因此cannibal(食人者)和Caribbean(加勒比海)二词其实源自同一个名词。
在中世纪晚期以及热潮渐缓的16世纪和17世纪,形容敌人有食人恶行于己极其有利,因为食人和鸡奸以及渎神的行径一样,都是违背自然法则的行为,犯此罪行者不受法律保护。
蒙田所撰的《论食人族》一文常被人引用,说明西方社会在历经征服美洲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和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运动的洗礼后,自我认知是如何彻底革新的。他表示,尽管欧洲有基督教教化和哲学传统的优势,但是让欧洲人自以为是、互相残杀的那一套虚伪道德并不比食人行为的道德水平高尚多少。在法国,宗教仇敌彼此凌虐、焚烧对手,形同“吃活人”。“我认为吃活人比吃死人更加野蛮……
食物经过重新诠释后,不再只是维持生命的物质,而被赋予象征价值和魔力,所以人要吃食物;人类发现食物具有意义。
主食几乎永远是神圣的,因为人不能没有主食,主食具有神祇的力量。虽说主食通常是由人耕种得来的,但此事实似乎并未折损其神圣地位。因为耕种即是仪式,是一种最卑微的崇拜仪式。人们天天在田里服侍谷物,弯下腰去耕耘、播种、除草、挖地和采收。当这些神明牺牲自己,进了人的肚子时,可以确知的是,神明霎时重生了。食用神明并非不敬,而是在奉祀神明。
被禁止食用的动物是在各自种类上反常的动物,爬行的陆生动物、四足的飞禽或猪与骆驼等偶蹄但不反刍的动物。
在大多数文化中,传统营养学都仰赖随意的分类,因此是不科学的,起码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科学。
不妨将它理解成一种转化魔法,类似于食人习俗的魔法:你吃了什么,就可以获得那东西的特质。
腌渍后还能保有适当维生素C含量的蔬菜只有酸圆白菜(sauerkraut),在18世纪早期只有荷兰海军食用,效果似乎不错。
一般来说,每个人都应尽量少吃,他应借由仔细的调查、文明的经验和观察,来找出自己仅需多少分量的食物,便可完全达到其体质所需的营养。他应当明白,只要吃过这个限度就是罪恶在一派胡言乱语的时代气氛下,新的科学发现一出现就落入骗子之手据说芹菜含有同样的激素,当草药煎来喝效果最好:煮上30分钟,“效果惊人”。[插图]不过另有一种说法:“在中国,多年以来的经验表明,芹菜有降血压作用。”[插图]这两种说法实在有些矛盾。
诚然,大多数高脂饮食的文化,特别是在那些爱吃饱和脂肪酸的地区,心脏病发生的概率确实较高,而这一概率在脂肪摄入量较少的社会则较低。可例外不胜枚举,这说明我们仍需进一步研究,而非一味禁食脂肪。
食物不只是可以拿来吃的东西而已;随着这项发现,革命展开了,而且还在继续进行。我们仍在不断地寻找新的方法,为满足社会效益而吃:以便和饮食与心态跟我们相同的人交往,和漠视我们饮食禁忌的外人划清界限;也重新打造我们自己,重塑我们的身体,改造我们和人、自然以及神的关系。
对饮食的执念是文化史上的波动,是任何健康食品都无力治愈的现代疾病。
有些则是天然的“食物处理器”,非常有用:反刍动物和食草动物可以把人类无法直接食用的能量来源,比如牧草、坚硬难吃的树叶和厨余,转变成我们称之为肉的食物。
在哥伦布第二次横渡大西洋的探险中,很可能是猪和马而非人把疾病从旧世界带至新世界,从而造成美洲原住民人口的锐减。
中国菜就不爱用乳制品,牛奶、黄油、鲜奶油,甚至不需乳糖酶即可消化的酸奶和酪乳都遭到中国人嫌弃,称之为野蛮口味。
我怀疑西方富庶国家对鱼的需求量大增是因为人们存有浪漫的成见,喜好这最后一种经猎捕而来的主要食物。
野生种群肯定会灭绝,因为养殖鱼是病原的携带者:由于养殖技术或处理方法,养殖鱼可以抵抗疾病;可是它们一旦接触到养殖场外没有免疫力的鱼群,必会带来一场大屠杀。
务农和养殖牲畜一样,是人类在物种进化过程中最早采取的强力干预行动:通过分类和挑选,以人为操纵的方式制造新的物种,而非任由天择。从历史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世界史上最大的革命,是一个新起点,其影响之大,只有16世纪的“哥伦布交流”(参见第七章)或20世纪末的“基因改造”技术(参见第八章)才比得上。
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人人平等的黄金时代,自然选择的演化过程本就蕴藏着不平等。
礼仪永远在演化发展,因为礼节的一部分目的就是要排除圈外人,要是有人闯入,打破了礼俗,就得重新制订规范。
这个事实是,食物和语言与宗教一样(或许程度更堪),是文化的试金石。
食物和饮食方式的传递在文化上的障碍如何被跨越或打破,是食物史上最令人好奇的问题。
这种移民风潮制造出中西合璧的菜肴,其中最恶名昭彰的是炒杂碎(chop suey),就是把竹笋、豆芽、荸荠等杂七杂八的蔬菜,加上肉片或鸡肉炒成一盘,这道菜是在美国率先开张的中餐馆的发明。
17世纪晚期,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试验研究煮过的糖的保鲜性,由此启发了莱布尼茨,后者改良他的几项发现,将它们应用于作战军队的食物补给。
工业化造就了不纯净、腐败和掺假的产品。然而在工业化时代,更加工业化却是唯一可接受的解决方法。
如今已有用黄豆做成的素肉,可是一个人如果拒绝吃肉,怎么会想要吃假装成肉的素菜呢?
史上任何以城市生活为主的文化,几乎都出现过供应现成热食给城市贫民的摊贩。
如是我闻
吃是一种文化,以保护火种为目的的围炉文化是聚餐社交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