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兰小欢
- 完成日期:2022.4.15
-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概览: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 评分:⭐️⭐️⭐️⭐️
- 类别:经济
书籍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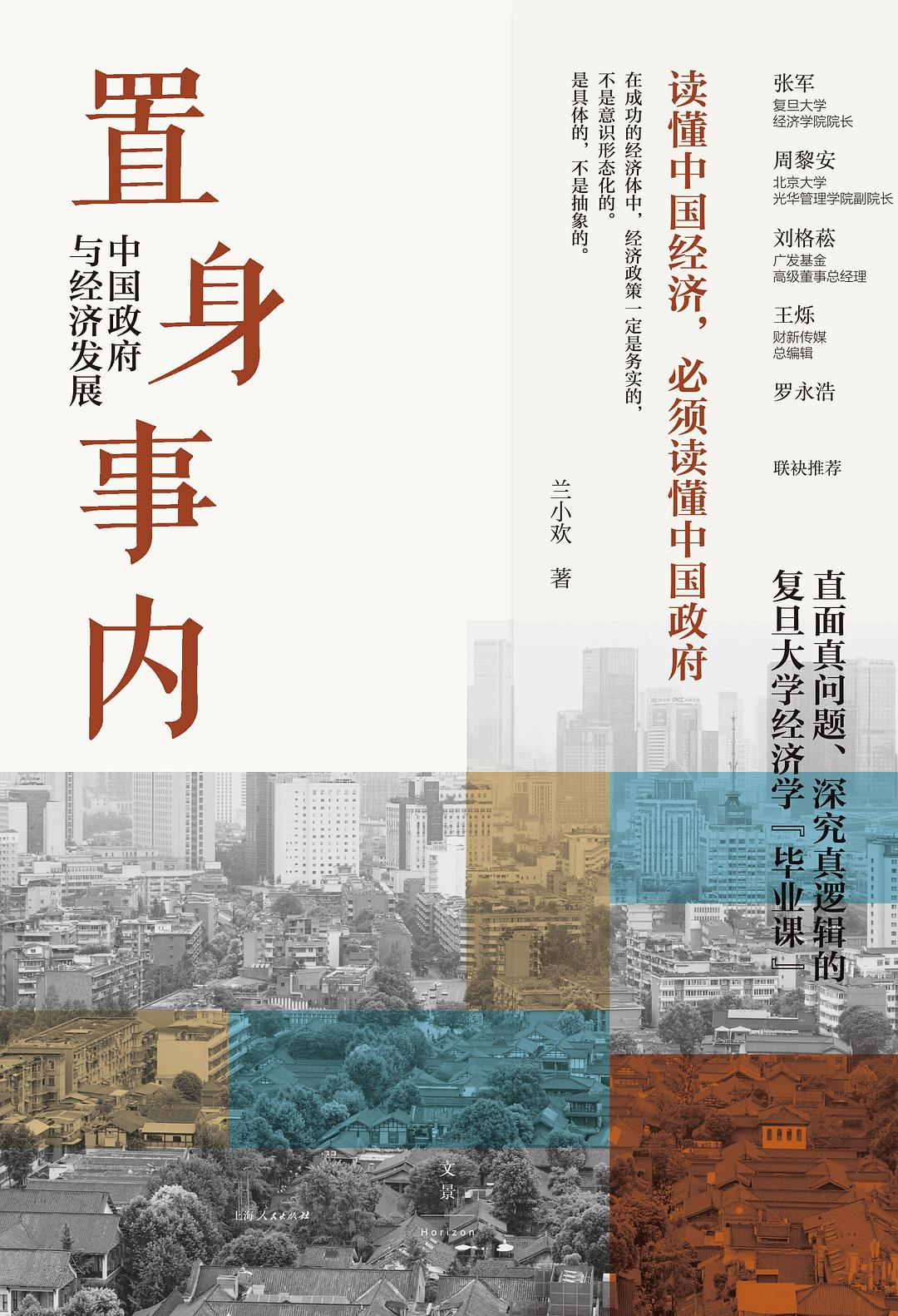
本书是是兰小欢多年教学、调研与研究内容的凝练,将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有机融合,以地方政府投融资为主线,深入浅出地论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笔触简练客观,并广泛采纳了各领域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解释微观机制,包括地方政府的基本事务、收支、土地融资和开发、投资和债务等;下篇解释这些微观行为与宏观现象的联系,包括城市化和工业化、房价、地区差异、债务风险、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国际贸易冲突等。最后一章提炼和总结全书内容。
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论述,作者简明地刻画了地方政府进行经济治理的基本方式,并指出,中国政府通过深度介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逐步推动了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以一种有别于所谓发达国家经验的方式实现了经济奇迹。基于对改革历程与社会矛盾的回顾与分析,作者也在书中对当前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与政府转型进行了解读,帮助读者增进对中国发展现实的把握。
书籍摘要
以公共物品的规模经济和边界为切入点,也可以帮助理解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分工上的一些差异。比如国防支出几乎全部归中央负担,因为国防体系覆盖全体国民,不能遗漏任何一个省。
地方政府是城市土地的所有者,为了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会把工业用地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转让给企业使用,并负责对土地进行一系列初期开发,比如“七通一平”(通电、通路、通暖、通气、给水、排水、通信,以及平整场地)。
这种“混合经济”体系,不是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政府和市场的简单分工模式,即政府负责提供公共物品、市场主导其他资源配置;也不是简单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模式。而是政府及其各类附属机构(国企、事业单位、大银行等)深度参与大多数生产和分配环节的模式。在我国,想脱离政府来了解经济,是不可能的。
本章讨论了事权划分的三种理论: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与边界、信息复杂性、激励相容。
不能脱离政府来谈经济,是理解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
香港中文大学金观涛和刘青峰的著作(2010)曾用“超稳定结构”来描述历经王朝更迭的中国古代社会,这一结构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大子系统组成。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官僚和儒生,是该结构日常运作的关键,也是在结构破裂和王朝崩溃之后修复机制的关键。世界历史上,王朝崩溃并不罕见,但只有中国能在崩溃后不断修复和延续,历经千年。
中国自魏晋以来出现“官吏分途”,即官吏虽同在官僚机构共生共事,但在录用、晋升、俸禄等方面相互隔绝。
我很喜欢两部国产电视剧,一部是《大明王朝1566》,一部是《走向共和》。这两部剧有个共同点:开场第一集中,那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们,出场都没有半点慷慨激昂或阴险狡诈的样子,反倒都在做世上最乏味的事——算账。
要想把握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动向,不能光读文件,还要看政府资金的流向和数量,所以财政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事权和财权匹配”的体制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也造成很多不良后果,催生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我国的基本国策决定了不能对所有权做出根本性变革,只能对使用权和经营权实行承包制,以提高工作积极性。财政承包始于1980年,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对收入和支出进行包干,地方可以留下一部分增收。
财政包干造成了“两个比重”不断降低: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而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低(图2-2)。不仅中央变得越来越穷,财政整体也越来越穷。
虽然地方预算内的税收收入要和中央分成,但预算外收入则可以独享。如果给企业减免税,“藏富于企业”,再通过其他诸如行政收费、集资、摊派、赞助等手段收一些回来,就可以避免和中央分成,变成可以完全自由支配的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因此经常给本地企业违规减税,企业偷税漏税也非常普遍,税收收入自然上不去,但预算外收入却迅猛增长。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分为三类: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如增值税)。同时分设国税、地税两套机构,与地方财政部门脱钩,省以下税务机关以垂直管理为主,由上级税务机构负责管理人员和工资。这种设置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干扰,保障中央税收收入,但缺点也很明显:两套机构导致税务系统人员激增,提高了税收征管成本,而且企业需要应付两套人马和审查,纳税成本也高。2018年,分立了24年的国税与地税再次开始合并。
公众所接触的信息和看到的现象,大都已经是博弈后的结果,而缺少社会阅历的学生容易把博弈结果错当成博弈过程。
成功的政策背后是成功的协商和妥协,而不是机械的命令与执行,所以理解利益冲突,理解协调和解决机制,是理解政策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各地烟厂、酒厂越办越多,很多地方只抽本地牌子的烟、喝本地牌子的啤酒,这种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也不利于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在2002年的所得税改革中,除一些特殊央企的所得税归中央外,所有企业的所得税中央和地方六四分成(仅2002年当年为五五分)。为防止地方收入下降,同样也设置了税收返还机制,并把2001年的所得税收入定为返还基数。
改革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之后应付一系列重大冲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汶川地震等)奠定了基础,也保障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如国企改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分税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
人们在乐观时往往会低估负债的风险,过多借债。当风险出现时,又会因为债务负担沉重而缺乏腾挪空间,没办法应对。
只要名义GDP(内含物价)保持上涨,债务占GDP的比重可能不是个大问题,至少对政府的公共债务来说不是大问题,可以不断借新还旧。(1)但对居民和企业而言,债务总量快速上升,依然会带来很大风险。
以按揭为例,穷人因为收入低,买房借债的负担也重,房价一旦下跌,需要先承担损失,直到承担不起破产了,损失才转到银行及其债主或股东,后者往往是更富的人。换句话说,债务常常把风险集中到承受能力最弱的穷人身上。
所以银行很少雪中送炭,却常常晴天送伞,繁荣时慷慨解囊、助推经济过热,衰退时却捂紧口袋、加剧经济下行。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机器变得越来越智能化,需要运用大量软件和服务,而设备本身的相对价值越来越低。所以大量投资进入了所谓的“无形资产”和服务业,而服务业更依赖于人的集聚,也就推升了对特定地段的住房和社交空间(即各类商业地产)的需求。
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大企业越变越大。理论上说,这不一定是坏事,若明星企业通过竞争击败对手、占据市场后依然锐意进取、积极创新,那么投资和生产率还会继续上升。
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国各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与企业规模的扩张,往往伴随着投资下降和生产率降低。
大量资金的涌入增加了资金供给,而企业投资需求不足又降低了资金需求,所以发达国家的长期实际利率(扣除物价因素)在过去40年间一直稳步下降,如今基本为零。(24)因为缺乏能获得长期稳定收益的资产,各种短期投机便大行其道,所谓“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房地产泡沫”一个接一个。
在缺乏增长点的情况下,央行给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但商业银行资金贷不出去,容易流向资产市场。放松货币条件总体上有利于资产持有者,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加剧财富分化,固化结构扭曲,使危机调整的过程更长。
只要学过经济学,都知道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能让国家整体得益。但整体得益不等于让每个人都得益。从理论上讲,即便有人受损,也该支持自由贸易,因为整体得益远大于部分损失,只要从受益方那里拿一点利益出来,就足够补偿受损方且有余。但在现实中,补偿多少?怎么补偿?往往涉及复杂的政治博弈。补偿可能迟迟落实不到位,最终是受益者得益越来越多,而受损者却屡遭打击。虽说平均值是变好了,但那些受损的人的生活不是理论上的平均数字,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抗和行动,这是保护主义的根源。
每一步都有人受益、有人受损,拼命争取和拼命抵制的都大有人在。就算能看清对岸的风景,也不见得就能摸着石头成功过河,绊脚石或深坑比比皆是。
经济发展必然要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重新分配利益,所以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政府的关键作用之一,就是调控改变速度的快慢。
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理解发展过程,因此必须理解初始条件和路径依赖,对“历史”的延续性和强大力量心存敬畏,对简单套用外来理论心存疑虑。
因此,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践者,“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是不会过时的精神。
他特别强调了“幼稚产业”保护承诺的“时间不一致”问题,也就是起初设计好了将来要“断奶”的保护,最终却迟迟无法“断奶”的问题。
虽然见过的问题和麻烦可以再写几本书,但经历和见闻让我对中国悲观不起来。我可以用很多理论来分析和阐述这种乐观,但从根本上讲,我的乐观并不需要这些头头是道的逻辑支撑,它就是一种朴素的信念:相信中国会更好。这种信念不是源于学术训练,而是源于司马迁、杜甫、苏轼,源于“一条大河波浪宽”,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它影响了我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我接受这种局限性,没有改变的打算。
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
如是我闻
置身事内,经济政策没有对错,只有特定时代的优劣,发展虽有前车之鉴,但也无法全盘照搬。 经济本就是个混沌系统,还与政治密切相关,宏观政策必然有其权衡和依据,并非张口就里的批评那么浅薄。 改革开放以来短短几十年的成就确是奇迹,感觉科学规律,发展过快不可避免带来许多问题,应该正视问题,解决问题,而非讽刺贬低。 最后一句很好,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