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Shawn

现在是晚上八点十分,这家瑞幸九点打烊,我只有一杯咖啡的时间来记录昨晚的“地下沙龙”,真的好想一口气写完,finish writing it in one sitting!昨天是糟糕的一天,因为不可告人的原因,我睡得很晚,又醒得很早,整天不在状态,一把年纪了我还是缺乏自律,迟早要死于睡眠失调。
轮到我主持地下沙龙,Anson 临时有事无法参加,我果断地提议会议“按既定议程”举行,绝非对 Anson 不敬,相信他能理解我的决定,我很尊重 Anson,一直欣赏—确切地说是仰慕—他的创作才华。家里隔音效果不好,不能畅所欲言,我前往附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户外站立一小时,中规中矩地(如果说不上可圈可点)完成了主持任务。
此次地下沙龙的核心议程是“选读作品讨论”,我推荐了三篇文章:
1、胡平:我们时代的见证文学—阅读廖亦武《证词》
2、The Mind of John McPhee|A deeply private writer reveals his obsessive process(《纽约时报》采访 John McPhee 的新闻稿)
3、The Art of Nonfiction No. 3(《巴黎评论》的 John McPhee 访谈录)
2023年1月30日22点整,“地下文学”的四位成员(Jennifer、Chin、宁想白和我)相聚 Google Meet,互道春节问候,我正要宣布会议开始,VPN 突然诡异地掉线,我方寸大乱,幸好重新连接后网络很稳定。
我在开场白里阐述了选读作品的推荐理由,过去几年我的阅读以英文为主,一时找不到值得推荐的简体中文作品,冒着被喝茶的风险,我分享了珍藏在 iPad 里的“我们时代的见证文学”,一本禁书的序言。两篇英语文章都是新闻/采访稿,非母语读者读来较为轻松,考虑到春节假期,我刻意回避了可能造成阅读障碍的虚构文学作品。
进入选读作品讨论环节,我让其他人分享阅读感受,竟然忘记先谈自己的感受,偏离了议程,尽管不用露脸,我还是紧张,四个人的会议足以激发我的公共演讲恐惧。
Jennifer 的发言让沙龙回到正轨,他从学术视角对文本做了细致分析,他的认真和对议程的尊重让我汗颜。Jennifer 显然精读了 The Mind of John McPhee 一文,他说“transcendence in purportedly trivial subjects”这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我搜索相关文本,发现整段话都很精彩:
Literature has always sought transcendence in purportedly trivial subjects —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s Blake put it — but few have ever pushed the impulse further than McPhee. He once wrote an entire book about oranges, called, simply, “Oranges” — the literary cousin of Duchamp’s urinal mounted in an art museum.
第二天,Jennifer 在地下文学的 WhatsApp 群进一步分享他的感受,略作修订后摘录如下:
我在寫作時,即便未察覺,一直本能的抗拒「虛構」或所謂「小說」,或許就是如柄谷行人的小書所寫,抗拒西洋現代文學的前提,「假裝」客觀的呈現「包裝後」的主觀,想要主觀,為何不直接主觀呢?而寫實小說的矛盾則是,想要寫實,為何不直接寫已經發生過的事呢?……所以讀到 The Mind of John McPhee,很本能地把非虛構寫作納入文學的討論,便是興奮的好奇,延續柄谷行人的想法,非虛構在美國如此受歡迎,或許是上述矛盾的解方。另外,對於胡平所謂「非美學化」我覺得如此有趣,也是因為柄古討論私小說時,說當時的日本人覺得小說「虛偽」,需要「自白」這種寫法,製造真實,讓我覺得說法上有近似的地方,覺得胡平的觀察很到位。
美国的非虚构写作群星闪耀,当然配得上“纳入文学的讨论”,重点不在于虚构或非虚构—我已厌倦这个话题,而在于“写”,即以何种方式推进叙事,这篇会议纪要至少有一千种写法,如果无需写成职场公文抄送任何人。
Jennifer 说他之前不知道廖亦武,我有些惊讶,不过想想也正常,喜欢下午茶的台湾年轻一代有自己的文学偶像,廖亦武的读者应该都上了年纪,比我还老……抱歉,我不能再谈廖亦武了,他是国家的敌人,“老大哥”正盯着我看!Matters 不是法外之地,翻墙有罪,谈论廖亦武罪加一等。
二月五日下午四点,我枯坐在檀溪路“闲叙咖啡”,面前的拿铁早已喝光,我去吧台要了一个保温水壶,用咖啡杯喝水,品尝深烘咖啡豆残留的焦香。上午我在天元世纪城“上野咖啡”写了一小时,家里无法写作,我被迫花着最后的存款泡在咖啡馆里写,压力巨大,写作随时可能脆断。
除了在 Mastodon 发布口水化的嘟文,我的写作很少一气呵成,这篇会议纪要越写越慢,我被困在非虚构叙事的迷宫里—“一千种写法”惹的祸,五天才写一千字。在瑞幸我只写了开头两段,后来不断修改,一杯咖啡的时间都不够热身,拉开“写”的架势。此次创作我已消费六杯咖啡、一杯奈雪的茶(太晚不敢喝咖啡)、一杯精酿啤酒(用酒精抵御咖啡馆的二手烟),ENOUGH IS ENOUGH!今天一定要写完。
Jennifer 之后是宁想白发言,她的声音很模糊,像蒙上一层浓雾,我在宁静的公园竖起耳朵也未能获取完整信息,直到议程过半,Chin 出场以后,宁想白突然摘掉耳麦,声音才恢复清澈。
宁想白选读了“我们时代的见证文学”,她也是非常认真的读者,在我看来毫不起眼的句子都不放过,我直言她在过度解读文本。宁想白认为“从狭义上讲,见证文学的作者必须是苦难与邪恶的亲身经历者,而不仅仅是在场的旁观者”这句话有待商榷,旁观也是见证,既然见证了,为何不能从事见证文学创作?她还质疑廖亦武写《证词》是为了“赢回在狱中失去的尊严”,尊严一旦被剥夺,还能写回来吗?
去年六月初,“德国之声中文网”采访身在台湾的廖亦武,报道的标题是“一本书对抗一个国家”,我看得热血沸腾,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那样写,宁想白给我泼了冷水,文学终究是无力的,对抗国家更是没有好下场。
Chin 的女中音充满磁性,我有些慌乱,无法专注地听她发言,未能履行 Jennifer 期待的“引导成员就选读作品发表意见”的职责,我只记得 Chin 提到写作的“结构”,她应该也读了 The Mind of John McPhee,我找到相关段落:
I asked McPhee why he is so obsessed with structure. He told me it was because his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 Olive McKee, made him outline all of his papers before he wrote them.
Every writer does some version of this: gathering, assessing, sorting, writing. But McPhee takes it to an almost-superhuman extreme. “If this sounds mechanical,” McPhee writes of his method, “its effect was absolutely the reverse. If the contents of the seventh folder were before me, the contents of twenty-nine other folders were out of sight. Every organizational aspect was behind me. The procedure eliminated nearly all distraction and concentrated just the material I had to deal with in a given day or week. It painted me into a corner, yes, but in doing so it freed me to write.”
John McPhee 一生痴迷于结构,他的方法很像为写作绘制“设计图”,听起来有点机械,但设计图让作者专注于更加具象化的写作任务,效率反而更高。
McPhee 在普林斯顿大学教非虚构写作,桃李满天下,他的硬核写作技巧滋养了众多活跃于西方主流媒体的撰稿人,包括颇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何伟在 Strange Stones 一书的献辞页赫然写着:For John McPhee。
Chin 的发言(就选读作品发表的正式意见)疑似因其他成员插话而提前结束,我开始本环节的总结性发言,大谈廖亦武,趁机发表恨国言论。
“你这样安全吗?会不会有人听到?”宁想白表达了担忧。
“我应该很安全吧,公园里没人,摄像头也听不见我说什么。”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经历了狱中的恐怖,作为知名诗人的廖亦武已经死了,再也写不了诗,只能“赤条条地”—有台湾媒体这样评论廖亦武的写作—写《证词》。
我曾经是公司白领,后来被职场淘汰,被社会抛弃,又被僵尸状态的婚姻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除了币值跌至谷底的 LikeCoin,我没有任何收入,对我来说写作本身就是残忍的(不写也很残忍)。我几乎放弃在 Matters 发文,一度纳入写作计划的读书笔记和旅行文学现在看来很可笑—它们太奢侈了,我的全部气力或仅够写“多余人日记”—属于我的“《证词》”。
Chin 说奥斯维辛之后也有人写诗,比如苏联的一位诗人。
“是不是布罗茨基?”
“不是他,是一位女诗人……”
“啊,阿赫玛托娃!”
前不久我正在读布罗茨基的散文集 Less Than One,第二篇文章 The Keening Muse 写的正是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年轻时写过很多爱情诗,经历了斯大林的“大清洗”,她依然坚持写诗,只是主题早已和爱情无关。
二月七日下午五点,檀溪路闲叙咖啡,我像喝药一样将杯中剩余的澳白一饮而尽,闲叙的澳白很苦,加剧我内心的苦楚,这是此次创作消耗的第十杯咖啡。
上午我在上野咖啡写作三小时,跌跌撞撞地推进叙事,收获数百字的草稿,“先找地方吃饭,下午去闲叙继续写,争取天黑之前定稿,最迟明天在 Matters 发文,又能挣一笔 LikeCoin—至少 Jennifer 会支持我。”
连续喝了太多拿铁,我决定换个口味,也换换写作的“手气”,不料下午的写作演变成一场灾难,我应该是走火入魔了,叙事摇摆不定,左右互搏,中午才将标题改成“一篇会议纪要和十杯咖啡”,很快又要修改,第十一杯咖啡已不可避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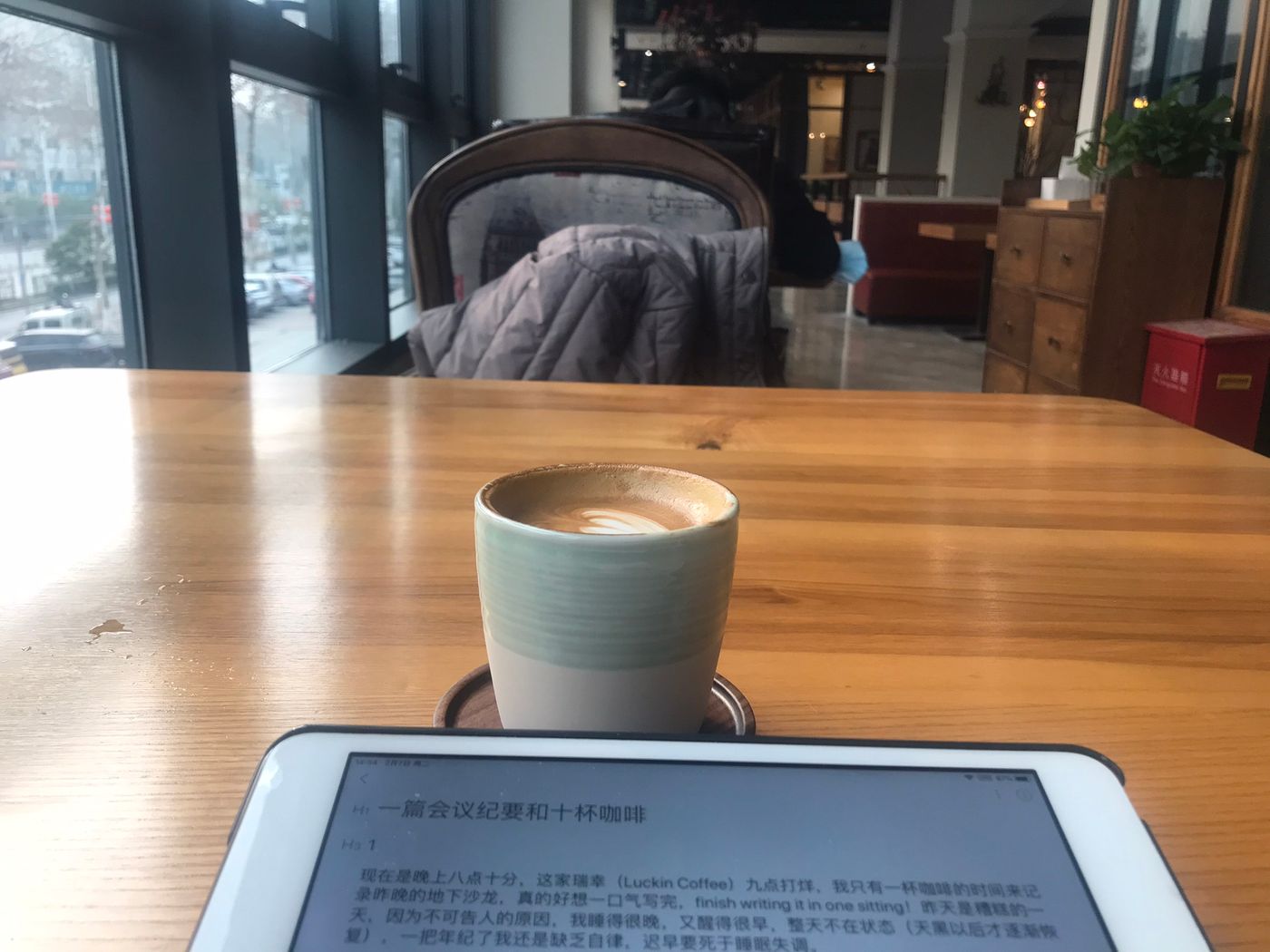
二月八日晚上七点半,闲叙突然响起钢琴声,琴师是我眼熟的一位年轻男子,原来他会弹钢琴,闲叙的钢琴并非摆设。装修升级后,闲叙俨然已是一家标准的西餐厅,供应品种齐全的牛排、披萨和高档红酒,“要是有钱在这里吃晚餐就好了,点一份牛排补充能量,满血复活,再写一小时或能完稿。”
我当然没钱吃闲叙的晚餐,微信账单显示我在隔壁的“一品锅贴”吃七元一碗的酸辣面。
完稿近在咫尺,我按耐不住兴奋,决定提前庆祝胜利,赶到上野咖啡喝了一杯二十五元的精酿啤酒—忘不了初次喝它时的味道。没钱吃饭,却有钱借写作之名无节制地饮用咖啡和啤酒,我的消费观真是极度扭曲。

二月九日下午高峰时段,闲叙有半数客人在密闭空间里吞云吐雾,为了写作我不得不忍受令人窒息的二手烟,暖气很强劲,我脱下外套还是觉得热,很羡慕服务生一身轻装,但我不便继续脱。
我使用一款叫“熊掌记”(Bear Pro)的软件写作,双手在 iPad 屏幕上指指点点,看上去很忙,没人知道我失业五年,二十多元的咖啡喝得我心惊胆颤。
研究表明,久坐等于慢性自杀,对中年男人尤其如此,闲叙的座椅偏软,餐桌偏高,坐着写一会就累。我坐不住了,不停地喝水,按摩眼睛,双手重重地划过头皮,搓揉太阳穴。我频繁起身去洗手间,有时仅为散步,这家闲叙面积很大,从座位去洗手间是不错的散步机会。
不到五点,身体和意志濒临崩溃,我果断地逃离闲叙,抵达江边,想尝试户外站立写作,无奈冷风呜呜地吹,气温接近零度,我不愿意伸手去掏背包里的 iPad。
写作是这世上最孤独的工作之一,没人理解,没人帮我,完稿的计划再次落空,很想找人诉苦,唯一潜在的倾诉对象竟是小我二十岁的 Frank,他的电话打不通,无所谓了,我没有具体的事情和他说,只是想找个大活人说话,来证明我还没死。
有必要声明一下,此次写作纯属自发、自愿的个人行为,一切后果(包括猝死)由我承担,不牵涉到地下文学—发起人 Jennifer 是无辜的。
遥想地下文学成立之初,Chin 和宁想白还未加入,Jennifer、Anson 和我举行视讯会议—那时还不叫地下沙龙,我们没有正式议程,以闲聊为主,想到哪说到哪,我和 Anson 不止一次地聊足疗(Jennifer 被动参与),讨论马、中、台三地相关行业的特色及差异。Jennifer 决定给“台北文学奖”投稿,忙着准备参赛作品,Anson 也表达了参赛意愿,我则自暴自弃,自绝于任何文学奖项。Anson 分享他在写作上的挣扎,说有个短篇写到三千字后放弃,我心想三千字已经很多,虚构作品我一个字都写不了。
我年轻时有过写小说的念头,后来发现自己缺乏虚构的能力和意愿,我在 Matters 写了十万字,都是非虚构。
2023年2月15日上午十点零六分,我坐在上野咖啡靠墙角的位置,正对玻璃门,前面那位男士在抽烟,左边隔着过道的四人座有两位穿银行工作服(深色大衣)的女士,她们点了四杯咖啡,一会有两位同事加入她们,我桌上的“早安咖啡”和开水都已喝光……不行,这样写下去没完没了,今天上午必须截稿,离店之前我要处理完剩下的草稿,它们被我晾了太久。
聊到布罗茨基和阿赫玛托娃时,地下沙龙已接近尾声,最后大约十分钟是我期待的闲聊环节,我试图拉进彼此的距离,询问其他人春节如何度过,不料遭遇小小的尴尬。Jennifer 只说了两个字—放空,宁想白说她遵循春节传统回了趟娘家,俩人均未分享更多细节,怪我,这个话题其实很私密,本不宜纳入议程。我主动和 Chin 聊她的“我們家的春節傳統”一文,感叹中国和台湾的巨大差异,“不势利的亲戚”对我来说像天方夜谭。
Chin 突然问我:“像你这样受过教育的人,中国的写作者,都在写些什么?想些什么?”
我的自尊得到极大满足,快要潸然泪下,说一个人“受过教育”是很高的评价,但我无法代表“中国的写作者”,我独来独往,不熟悉其他作者。
我不忘发表恨国言论:“这个国家就是文学洼地,原因各位都懂的。”
我在最后一刻感谢 Jennifer 支持巨额 LikeCoin,他自掏腰包给其他成员发放春节福利,已经不能做得更好。
此次创作共计消费二十五杯咖啡、三杯精酿啤酒、一杯奈雪的茶,鉴于没有明确的截稿日期,不排除我故意拖延交稿,拖延过程中新的想法不断涌现,叙事路径也随之改变,从而加剧拖延,弄假成真,走火入魔。咖啡馆的二手烟确实很讨厌,可谁叫我不吸烟?我应该是错怪了闲叙的椅子,咖啡馆的椅子差不到哪里去,腰才是关键,给我世间最舒服的座椅,我的腰也很难坚持写作三小时。